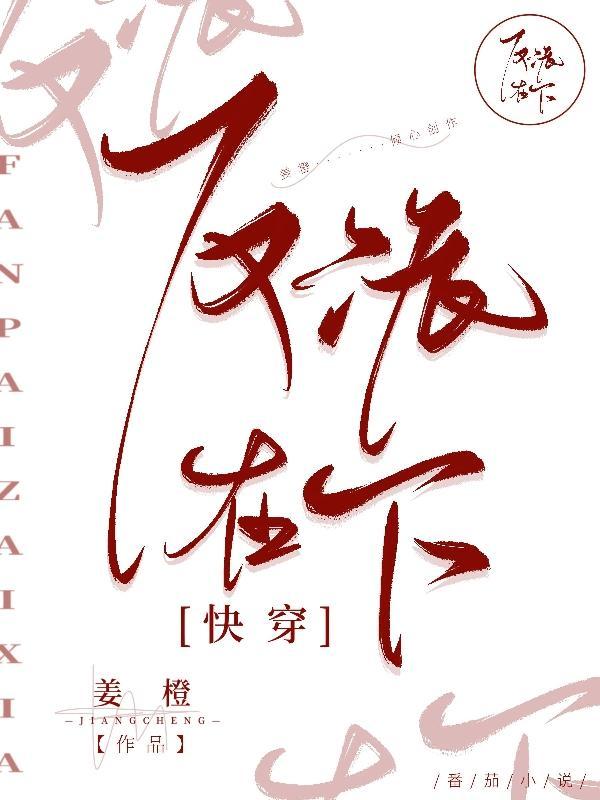凤阅居>十七之后半黄梅子雨 > 第12章(第1页)
第12章(第1页)
顾雨崇眉梢微挑,“嗯”了声,拉住陈山润的手,穿过连排的院子,走上桥,落叶铺满地,风湿漉漉的,像回到老家漫长无边的雨季。
陈山润欲言又止,想问点实情,又怕顾雨崇不答,凝了凝眉,抬头,薄雾弥漫的伦敦,河对岸,圣托马斯医院亮着急诊灯,想到五年前,他刚从县医院到市医院,病房还没安排,顾雨崇忽然消失,半个月后回来,瘦了一圈,怎么问也不回答,最后在窗前晕倒,才知道他被亲妈虐待。
陈山润重重踩了一脚落叶,刚刚在家里问半天,反倒自己迷糊了,到现在都不知道他和白拾怎么认识的,还有他又摊上什么事了,让黑帮的人追着不放。
套他的话果然不能急,得慢慢来。
“顾雨崇,你上个月几号来的伦敦?”
“八号。”
陈山润点头,“正好是我做手术那天欸。难怪我打麻药的时候闻到了机场咖啡店的味道,你是不是上飞机前点了杯拿铁?”
“没有。”顾雨崇偏头看他,陈山润抿了下唇,正要开口,顾雨崇指着拐角,亮着灯的中餐馆,“我们到了。”
推开门,江南古典的装修风格,刘君越站在光影里,墨色旗袍染上竹叶影子,像水墨画里走出来的女人。
她今年不过四十有余,鬓角却长满了白发,月华如旧,美人迟暮,说的不过是她。
“君越姐,好久不见。”
刘君越视线从陈山润脸上扫过,盯着顾雨崇,问:“这个点来我这,是有急事,还是单纯吃饭?”
“吃饭。”
“哦,”刘君越朝陈山润抬了抬下巴,“这位是?”
“老同学,来伦敦找我玩的。”
刘君越颔首,领他们坐进小包厢,“想吃什么?”
顾雨崇看着陈山润,等他回答。
“给我们整两碗面就行了。”陈山润指着墙上招牌,清汤牛肉面的海报有些泛黄,红黄标价,老家面馆常见到。
刘君越朝后厨喊了声,关上门,坐在他们对面。
陈山润有些茫然,顾雨崇在手机上敲了几个字:“君越姐是我妈妈在红灯区认的妹妹,五年前搬来伦敦,盘下这家店。”
陈山润眼皮一跳,目光移到刘君越脸上,听她道:“疏城这些年变化大吗?”
“好多房子都拆了,不过它下面的淮江县还是老样子。”顾雨崇自顾自倒着茶,喝了口,隔夜凉茶,他皱眉,把陈山润面前的杯子移到角落里。
刘君越恍若未闻,简单寒暄几句,再也坐不住,朝他示意,“你出来一下。”
“嗯?”顾雨崇指尖蜷缩,轻敲桌面。
刘君越又招呼一声,他只好提醒陈山润别喝茶,别乱走,跟着出去了。
半明半昧的天空,月亮还挂在头顶,顾雨崇环视一圈天台,视线定格在二楼包厢。
毛玻璃勾勒出陈山润轮廓,影影绰绰,他轻呼一口气,也不知怎么回事,一颗心定在他身上,七上八下的,生怕下一秒他消失,生怕这一眼,就是人生的最后一面。
天台的风呼啸而过,刘君越踩着高跟鞋上楼,递出一封信,邮戳上印着紫罗兰花,和何繁给的一模一样。
“象堡那边前两天死了个女学生,我查了一下,和九榕树钱庄有关。”
顾雨崇盯着邮戳,没有接。
刘君越从兜里翻出u盘,一齐塞到他手里,“还有,白拾的话不要全信,死的女学生是她医院的实习生,遇害前半小时她们见过面。”
晚秋(1)
“谢谢你,君越姐。”
顾雨崇收起u盘和信封,又道:“天亮后我先去探白拾的口风,她身上不止这一处疑点。”
刘君越点了支烟,夹在指尖,“怎么?你也查到什么了?”
“她瞒着我让魏雪生去了趟疏城。”
刘君越眉头一下子皱紧,“她叫那丫头回国做什么?”
“和‘伦敦眼计划’无关,和‘婚礼’有关。”
顾雨崇简单概括,风把领带高高吹起,上面还有陈山润打结时留下的褶皱,他轻轻抚平,又道:“老先生还不知道这事,白拾这些日子一直待在老宅,没回过休斯顿庄园。”
“别再我面前提老先生。”刘君越咬紧牙关,神经紧绷,高跟鞋踩进水泥坑里,抬了好几下脚,才拔出来。
顾雨崇走到她跟前,挡住暗红色的灯笼,唐人街错综复杂的巷子,道:“君越姐,苦日子都过去,你再等一等,他们就快倒台了。”
刘君越没说话,猛吸一口烟,额角抽痛,片刻才道:“象堡我自会帮你盯着,那女生的背景我也调查出来了。”
“多谢,回家我拆信仔细研究。”顾雨崇颔首,二楼光影闪烁,陈山润不知去向,他呼吸一滞,朝楼下走去。
“先别急着走,你把信拆开,里面有女学生的遗书,写的蛮古怪的。”刘君越拦在他面前,拿烟的手指了指他大衣口袋。
顾雨崇抿唇,掏出信封。
刘君越继续道:“那女孩是个艺术生,大二gap一年在白拾公司做广告实习,前天下午她在arsenal咖啡店和白拾见完面,半夜就从公司顶楼跳了下来。”
顾雨崇瞳孔骤然缩紧,撕开密封条,“公司的广告部一直外包,hr不会随便给外包员工办工牌,她跳楼前可能见过什么人,给了她工牌和顶楼天台大门的密码。”
刘君越点头,掏出手机,借着屏幕亮光,看信里内容。
“我们把高三的那一场考试看得太重,往后的十余年都活在选错题的梦魇中。”
顾雨崇从上扫到下,皱起眉头,指尖摩挲信纸边缘,纸张光滑,拐角有道折痕,被胶带粘住,里面像是藏了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