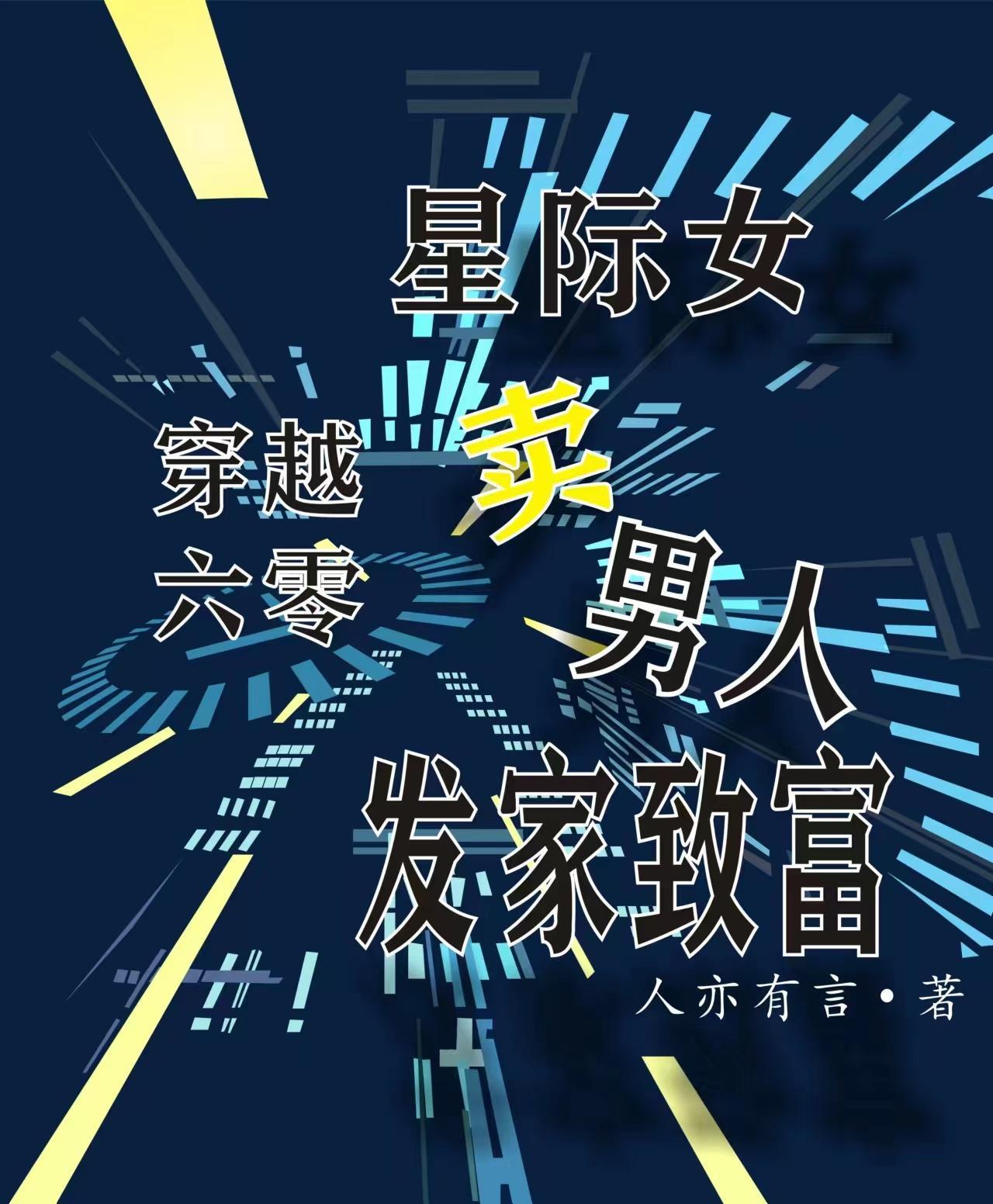凤阅居>钓系美人被迫和亲后 > 第42章(第1页)
第42章(第1页)
斯钦巴日深吸了一口气,他紧咬着牙关,额角青筋狂跳:「奸细……他是个屁的奸细!」
萨仁抬起头看向他,正巧斯钦巴日也抬起头,那双幽绿的眼睛变得极为黯沉,似乎酝酿着风暴,又仿佛蕴含着更深的什麽,只是那太复杂了,萨仁看不大明晰。
他们赶往公主帐,正巧有人将那游商夏人的尸身给扔出来,「噗」的一声闷响,伤处迸溅出大股大股还温热的鲜血,溅在斯钦巴日的络鞮之上。
萨仁有察觉到,当斯钦巴日目光落到那夏人身上时,呼吸好似停滞一瞬,反覆被吓住了似的——
这实在罕见,也实在奇怪,在战场上杀人如麻的斯钦巴日怎麽会被这样一点血给骇住。
愈离近帐子,里头的喧嚣声便愈响亮,「哗哗」的鞭子声听的人肉疼,只是令人惊异的是,里头并无怜枝凄厉的哭声,反倒是一大片的大夏贵族的叫喊声——
此时走在最前头的几人已觉出不对,斯钦巴日瞳仁倏然一缩,三步并作两步的跨上前,「哗啦」一下拉开帐帘——
那场面几乎要叫萨仁的眼珠子都掉出来了,一大群大夏贵族抱头鼠窜,鬼哭狼嚎。
而不久前还涕泪横流的沈怜枝穿着一身被抽的破烂的衣裳,满身是血的踩上苏日娜面前的案几,扬手就往她背上抽了一鞭子。
他披头散发,从头到尾都脏乱不堪,那张苍白的脸,不知是真的浮现出了红晕,还是被血染红的,沈怜枝拎着鞭子,几乎是有些狰狞地说:「这是还你的。」
斯钦巴日也怔住了,跨出去的步子也没收回来,呆立在原地,他看着沈怜枝,看着自己这个,几乎让人认不出来的阏氏,心中震惊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
在他心里懦弱的丶遇事只会落泪,只要稍微吓一吓就会没有脾气的阏氏,那样的一个人,怎麽会提着鞭子,就这样毫无顾忌地,往连他都要给几分薄面的苏日娜身上抽。
他无法想像,此刻这一片的狼藉,这一群混乱的夏人,他暴怒的姐姐,悉数因怜枝而起……怎麽会是他的阏氏呢?
斯钦巴日在来时想了许多,他想他可怜的阏氏一定会哭泣丶一定会求饶,在见到他後一定会求他救救自己,可是现在,老天将事实摆在他面前。
事实告诉他,他对怜枝的一切设想都是错的——他不是窝囊废,他拎着鞭子,他也会暴起。
斯钦巴日一颗心在胸腔中狂乱地撞击着,跳的几乎比他砍下那个叛乱部落王的头颅时还厉害,那颗心脏好似要撞开他的胸膛了——一股热血从脚底冲到头顶,他简直头皮发麻。
这心跳,不是因为愤怒,也不只是震惊,好似还掺杂了激昂——就好像看到绵羊长出獠牙那样,总是令人惊奇的。
这时怜枝转过头来了,他隔着帐中混乱的一切与斯钦巴日遥相对望,那一眼……那是怎样的一眼?
极度的恨丶疯狂丶不甘,像熊熊燃烧的烈火,可又怆然丶悲凉,宛如一条已乾涸的河,这深深的一眼,几乎要将斯钦巴日的灵魂都给吸进去了。
沈怜枝笑了笑,斯钦巴日一直觉得他哭得勾人,却不晓得怜枝笑起来也是美的,他没说什麽,好似很累了,扔了鞭子——
在他倒在地上的前一瞬,斯钦巴日终於从那「会心一击」中回过神来,他冲过去,接住了晕过去的怜枝。
怜枝并不沉,可斯钦巴日接住他时,双手却一直颤动,从帐内走到帐外,短短一程路,他想了许多,从初见到现在。
他以为自己早将沈怜枝看透,却没想到自己其实根本不懂他。
旭日干替他将帐帘掀开,一股沁凉的清风迎面吹来,他睁开眼睛,只见绿草萋萋,随着拂来的春风摇曳舞动,这广袤的草原,像是一片连着天际的丶青翠色的海。
其实斯钦巴日早就知道冬去春至,可不知何时起,春草长得这样高了。
原来在无知无觉中,草已长得这样高了。
而他今日才发觉。
***
怜枝被好生安置在王帐之中,在公主帐中发的那一顿疯已透支了他的馀力,他受的伤要比小安子重的多。
小安子身上只挨了两鞭,可他扑在小安子身上,不知挨了多少,背上不知还有没有好皮肉——萨满巫医扛着一个羊皮药袋过来,跪在了怜枝的榻侧。
她将羊皮药袋放在兽皮毯上,解开结口,药袋展开後便成了一张巨大的羊皮,羊皮上画了各种古老的图腾。
巫医越过羊皮上的一众草药,去拿祭祀用的器具,神神叨叨地念着咒语。
斯钦巴日就站在沈怜枝榻边,一刻不离,见巫医还有这装神弄鬼的心思,气不打一出来,毫无敬畏之心地夺过她手中的祭祀骨棒。
他瞪着眼睛:「别做这些没用的,还不为阏氏上药!」
夏人医治前要求神是风俗,不过斯钦巴日可不管这麽多,也等不了,他是单于,萨满巫医也只能不满地撇撇嘴,却去取药草,捣出药汁来了覆在沈怜枝的伤口上。
几个侍仆迎上去,想为阏氏翻身脱衣,偏偏单于凶神恶煞地站在边上,像个活阎王,使得她们几个怎麽也做不好,手指时不时戳碰到阏氏伤处。
斯钦巴日生气地「啧」了一声,将她们都赶走了,居然道:「本王亲自来!」
几个侍仆便退开,候在边上眼睁睁地看着平日里坏脾气的单于将阏氏小心翼翼地抱到怀里,再为他脱衣丶翻身——几个侍仆悄悄地对视一眼,都从她人眼中看出惊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