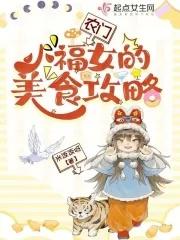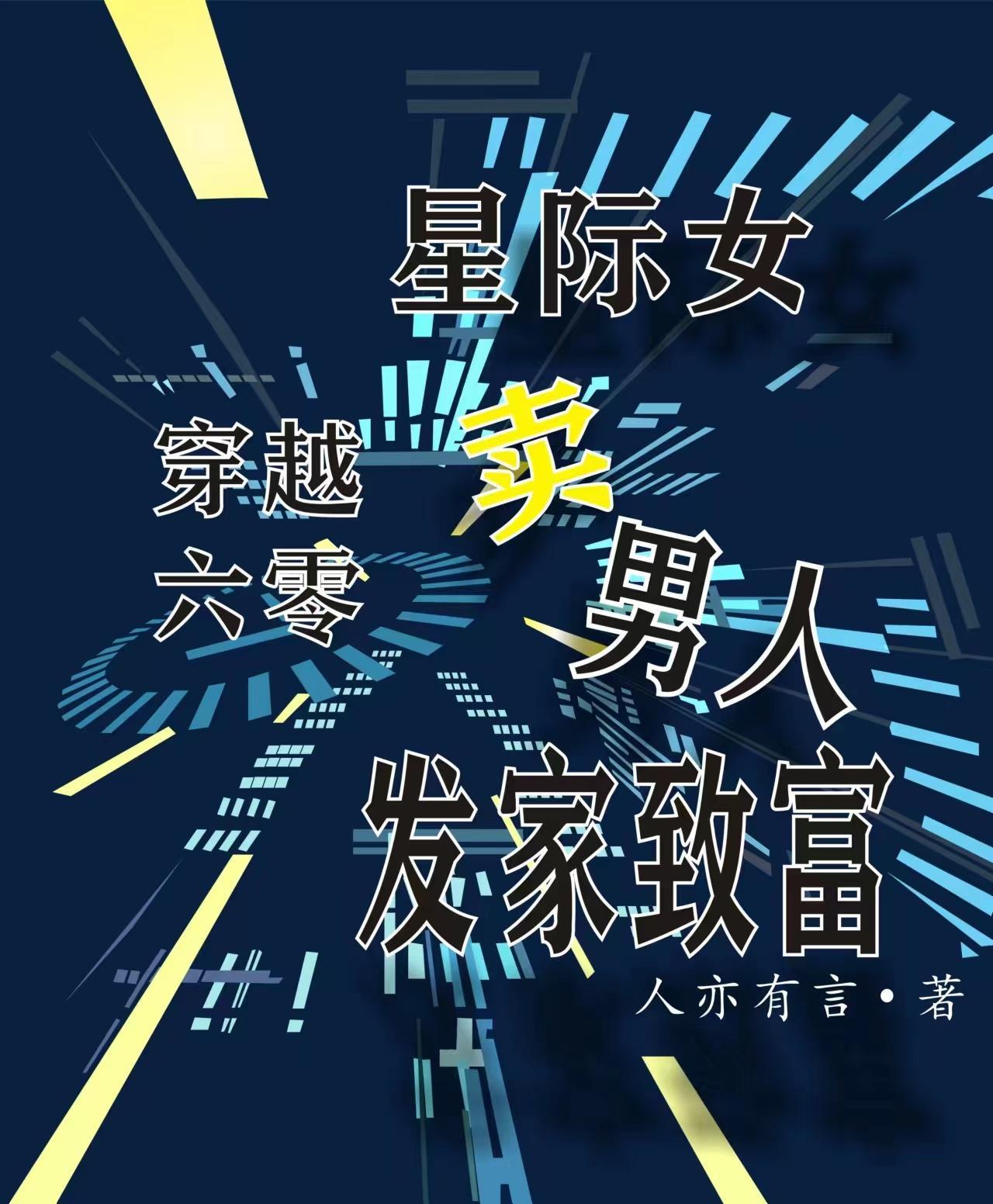凤阅居>老城街小面 > 第84章(第1页)
第84章(第1页)
关键是还挺香。
这罕见又丰富的吃食把那厢军都看愣了。
他抬眼看了看沈济。
沈济也回看向他,无辜地眨了眨眼。
“你这……难不成还预备在里头煮汤饼吃?”厢军纳罕,把那碗翻了翻,甚至把炸干的汤饼都掰成了两半,的确是没有夹带东西,他忍不住提醒道,“里头可没有炉子,更没有炭火,每人只供一壶热水。这汤饼是万万煮不熟的。你还是趁还没进去,赶紧让家人买上两个饼子吧!否则你这一日必要饿肚子了!”
“多谢军爷,热水便够了。”沈济深深一揖,想了想,还不忘道,“我家是金梁桥杨柳东巷开汤饼铺子的,日后官爷有空,一定来尝尝,我阿姊做饼的手艺实乃一绝,您来了绝不后悔。”
阿姊说等房子铺了瓦,便不赶早市去摆摊了,家里的铺子要开张了。她这几日又去杨老汉那儿定了好些桌椅板凳、条桌、柜台面等,又去定了一窑刻上了“沈记”二字的粗陶碗具,已经预备起来了。
沈济一直惦记着要帮衬阿姊,因此逮着机会便为家中的铺子宣扬起来。
这人既然不听劝,便随他去了!那负责搜检的厢军将那盖儿随意扔了回去,摆摆手让沈济进去了。而他望着那小童子离去的背影,也十分无语。
让你来这考学的,还拉上客了。
但又搜检完好几人后,这厢军总觉着心痒痒,只感觉这鼻子根还是能闻到那童子考篮里辛香味儿。
怎的这汤饼还未下锅便这么香?到底拿什么做得?以往竟没吃过,他又有些怀疑动摇了起来。
真如其所言那么好吃?
回头休沐……不如……真去试试?
方便面香
眼看着济哥儿顺利进去了,那小身板随人潮被国子学高高的门洞吞没了,很快便不论垫脚伸脖皆瞧不见了。沈渺松了口气,忙背起背篓四下张望,预备抓紧寻个好地段设摊。
国子学这“辟雍书院分校区”虽设在城郊,四下却并不荒凉。
驿道宽敞,黄土被压得十分紧实,若无快马疾驰而过,甚少烟尘激荡。驿道两边还遍植棠梨,如今正是花云团簇、郁郁葱葱的时节。沿着书院的围墙下,还间错着设了几处游廊凉亭、亭边点缀几棵高大的松柏、假山叠石,清风徐来,好生清雅。
但如今因童子试,辟雍书院门前停满了各色牛马驴车,不少仆从牵着牲畜靠着车等候,也有走着来的、如李家一般推着土车子来的,如沈渺一般挑着担子来做买卖的小贩更是数不胜数。总之,如今人流不息、人声鼎沸,实在喧闹非常。
厢军按着佩刀,夹在其中走动巡逻,早已没了那份清静的书香之气。
沈渺环顾一周,在书院不远处的驿道附近,总算寻到了个好位置。这儿地方在一棵高高的海棠树下,枝繁叶茂,晒不着日头。面朝人来人往的驿道,斜后方便是那挤满了人的凉亭与游廊,在此侯考的童子父母亲眷都一窝蜂在里头歇息呢。
她将背篓就地放下,先抽出两张小板凳来,便将里头一个个油纸包好的欧包用藤筐装好,背篓倒扣在地上,便成了张桌子。
她与湘姐儿一人一张板凳,坐在树下,有一搭没一搭地吆喝。
“新鲜出炉的炊饼哎,紫袍金带大炊饼哎!好吃好兆头!又香又软的大炊饼哎——”
她吆喝一句,湘姐儿也脆生生、奶乎乎地跟着吆喝。童声稚嫩,姐妹两个,大的生得模样秀致,小的扎着两个揪揪,奶团子似的可爱,倒吸引了些人来围观。
沈渺趁机拆了一个,用随身的菜刀切成丁子,又吆喝一声:“先尝后买,不吃白不吃,不买白不买嘞,过了这个村再没这个店——”
有便宜不占大傻子,很快便不少人围了过来,见藤条筐里一个个模样讨喜、颜色紫中金黄的炊饼,有人尝了不免动了心,问了价儿,虽有些贵,但……
那梳着妇人发髻的娘子牵着自家要应考儿子,有些犹疑地瞥了眼这卖饼的小娘子。
“吃了一准才思敏捷,日后好当大官呢!”这娘子笑起来眉眼弯弯,与她手中的炊饼一般讨喜,声音清清脆脆,吉祥话张嘴又来,“讨个好兆头,祝小郎君逢考必胜,吃得好考得也好,给您包上?”
这话太动听,那妇人终于没多犹豫,从随身的小布包里掏了钱,最后又道:“给我包两个!”
随后她与儿子便站在小摊儿前分吃了一个,母子俩轻咬一口,便惊喜地对视了一眼——这炊饼好生不同!初入口只觉粗粝得近乎质朴,但再多嚼几下便觉麦香满溢、甜意微蕴,拂过味蕾的桑葚清香与炒香的花生相佐,令人不免回味再三。尤其这炊饼表面还残留些被烤得褐黄的麦麸,吃起来还带着一丝秋栗初熟的绵密感。
于是做母亲的年轻妇人顿时决定不再多吃了,她连忙将剩下的好兆头炊饼塞进了儿子的烤篮里,急匆匆赶着要进去赴考。
当然也有谨慎的,自家带了吃食,嘱咐孩子不许吃外头的东西。但大多尝过了都忍不住买——毕竟除了好兆头,个中滋味才是留下食客的真实缘由。
沈大伯的驴车出现在沈渺的小摊儿面前时,沈渺正热火朝天给人包饼,一抬头,便看到了趾高气扬的伯娘丁氏与沈大伯,还有才几日不见,便又胖了一大圈的海哥儿。
海哥儿睡眼惺忪,眼皮微肿,仿佛是刚从床榻上揪起来的,圆胖的身子被裹在一件喜庆的绣着排鹤上云霄的绯红绸缎衫子里,好似个发酵过头的老面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