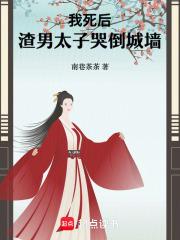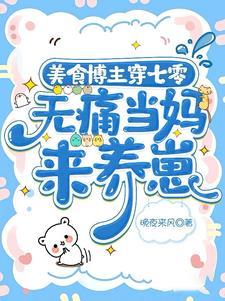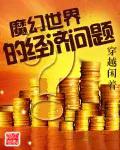凤阅居>角色创造类是什么意思 > 何谓戏剧作曲家(第1页)
何谓戏剧作曲家(第1页)
何谓戏剧作曲家?
在一部戏剧作品中为音乐找一个合适的定位并非易事。这恰恰因为音乐自身即是一门相当独立的艺术。音乐同样可谓“更好的”“理想的”生活的化身。音乐载着我们在节奏中前行,它有助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情绪会随着产生某种“气压”的旋律而变化;即使死亡,在音乐的陪伴下也显得容易一些,否则为什么全世界所有的军队都拥有出类拔萃的军乐团?音乐不仅是世界上最独立的艺术,也是最复杂、最抽象的。它无须借助任何外力即可充分表达自己,然而它是作为辅助手段被引入戏剧作品的。它的巨大力量必须服从于作品的通盘考虑。
所以说,在戏剧作品中纳入任何现成的,并非特意为之创作的音乐作品是个巨大的错误,哪怕这音乐确实遵循了纯粹的音乐法则。他们试图把音乐硬生生地塞进作品中,削足适履,重新编排。一般说来,这样做会引发导演和作曲家之间的种种误会。作曲家奉行音乐理论、音乐结构与音乐和谐的法则,导演和演员恪守的则是戏剧理论、戏剧结构与戏剧和谐的法则。这两者分属全然不同的领域。
为什么大多数歌手都是蹩脚的演员呢?因为他们必须把自己彻底交付给音乐法则,为此不惜牺牲生活的真实。依赖管弦乐队或者独奏乐器,借助铜管乐器或者弦乐器破空而来的音符
,表达昂扬激越的情绪,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人类的精神要表达同样强烈的情感,却是通过意味深长的沉默、无声胜有声的停顿来实现的。音乐法则要求演员和管弦乐队都把握住铜管乐器奏出的强劲有力的音符,为此他要付出全部的精神力量和身体力量,把他从“正在经历的角色”里拽出来,而那正是创造性演出中唯一的大事。另一方面,如果演员对角色的“精神阐释”倾注了过多心力,他通常会被指责忽视了音乐,对作曲家过于轻慢。夏里亚宾#pageNote#0就曾频频为此而受责难,因为他在舞台上一直遵循着自己的精神至上的法则。
戏剧有个惯例,就是管弦乐队于幕间休息时在乐池里、在垂落的幕布前演奏。你会看到乐手们信步走进乐池,彼此致意,擤鼻涕;你能听到他们谈论各自的私事,给乐器调音。换言之,我们眼睁睁看着他们冒犯了基本的戏剧问题——戳穿了戏剧的神秘性。为什么我们不应该目睹演员当众化装、穿戏服呢?为什么我们看不到置景工布置舞台呢?戏剧演出间隙的音乐的确与之不协调。严肃的戏剧和幕间演奏的欢快旋律——哪怕出自优秀的作曲家之手——之间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在歌剧以及轻歌剧中,音乐占据了主导地位。戏剧彻底听命于乐队指挥的指挥棒,即使它与“生活”的指挥棒彼此扞格。在这样
的例子中,戏剧的艺术从属于音乐的艺术,音乐的艺术拥有清晰协调的理论、经久不衰的法则;而这种娱乐性质的戏剧,无非是一个大杂烩,剧作家、演员、设计师和导演各自为战,然后再把他们的工作成果煞有介事地拼凑到一起,既没有连贯各环节的整体目标,也缺少明确的法则和规定,因为——“在戏剧中,诸事俱可为”。
另一方面,在戏剧作品中,音乐的情形则截然不同。首先,即使拥有扎实的理论,音乐也必须完全服从戏剧作品的主要问题。其次,在真正的创造性戏剧中,音乐仅占据次要地位,即或不是仅仅充当背景,也不过是整部作品的色彩之一,这一点必须被彻底理解。再次,配乐里乐器的数量与种类,以及某一特定乐器的音调强度,必须与作品主调的整体强度相一致。
我们不妨以霍普特曼#pageNote#1的《翰奈尔升天》(TheAssumptionofHannele)为例。这部剧的主要问题是佑护一个孩子的灵魂,表达对上帝的热烈虔诚的信仰。音乐伴奏中,有天使的合唱、基督的声音、神智谵妄的孩子的乱梦……我们在此可否动用大型管乐队呢?万万不可。
《哈姆雷特》结束于这位丹麦王子的葬礼。#pageNote#2为了营造更强烈的印象,在此使用军队葬礼进行曲是切合情境的。谱写这首进行曲是否应该遵从音乐理
论的所有条规,展开主题,抵达高潮?换言之——它是否应该构成一个独立的、完整的音乐作品呢?不,我们只需要时不时地听到几段和弦,足以为我们制造出葬礼的完整印象,增强因英雄之死而生出的悲悼之情就可以了。
要描绘《李尔王》中的暴雨,最佳的方式就是借助音乐的媒介,但是我怀疑,虽说我们的音乐文献中对“暴雨”的呈现数不胜数,却未必有适用于这一场戏的。的确,无论饰演弄人或李尔王的演员多么伟大,他的声音总是会淹没在四把长号的声响中,而这一场戏的重中之重——一个丧失了一切,在这样暴雨滂沱的夜晚无处容身的老人的忧伤——会被抹杀。
另有一种音乐的可能性,运用到戏剧作品中颇有优势,有时还会成就斐然。这就是用不同的声音装置而非乐器发出的乐声,描绘生活的种种现象。对于这一领域,我们当代的剧院其实所知甚少。莫斯科艺术剧院在排演一部戏时,要寻找能表现春之萌动的音乐。这是个童话——从戏剧结构来说,这一场戏至关重要。它是这一幕的主要问题,能否成功地表现,并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关系到全剧的成败。他们日复一日,下足功夫,在全世界的音乐文献中搜寻翻找,寻觅合用的内容,却是徒劳,一无所获!戏剧作曲家尝试专门为之谱曲,绞尽脑汁,结果总是
让人叹气——音乐要么太弱,要么太强,足以摧毁这一异想天开的场面。然而对这特别的一幕,演员的表演却精彩绝伦——舞台上仿佛充盈着真实的春天,你几乎能够嗅到松树树脂的气味、牧场青草的芳香,在这美好的春日晨光中,一切都轻盈而又警觉——但是音乐使他们的全部努力付诸东流。音乐是抒情而伤感的,小提琴拨奏曲依循着戏剧中的春天应该甜美宜人的惯例,却仿佛与真正的春天两不相干。巨大的失望笼罩着剧院。突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灵机一动,建议转而求助于第一手音源——大自然。于是他们开始分析:大自然在春天会提供什么音乐呢?人们在黎明的田野或森林中会听到什么音响组合,什么乐器才能够再现这些声响呢?事实证明,大自然的春之声浩如烟海,要想再现它们,必须为每个声响都设计一种特殊的乐器。
这里列举一些他们所找到的大自然在春天会有的声响:树叶沙沙作响,树木萌发嫩芽,枝丫彼此碰撞,树木嘎吱作响,风嘶嘶掠过,雨滴淅淅沥沥落在大片的牛蒡叶上,昆虫嗡嗡,鸟儿啁啾,鸭子戏水,流水潺潺,再加上仿佛来自一个遥远的村庄的一系列嘈杂的声响。经过苦苦琢磨,他们打造出了几件可以制造这些声响的乐器,作曲家根据音乐的法则把它们编排成有规律的音阶,再用一支普
通的长笛吹奏出牧羊人的曲调作为背景——此时,也只有此时,彻底呼应演员心境的音乐才算大功告成,他们孜孜以求的感觉才找到了准确的表达。
这部戏首演之后,音乐评论家和作曲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努力取得了何种结果——但是观众却说,在演出期间空气中分明洋溢着春的芬芳,并好奇地询问这是使用了什么戏法。剧院成员们但笑不言,因为他们深知,他们剧场里的气味与其他成百上千个剧场里的并无二致——可他们同样深知,他们是大自然的忠实信徒,追随着大自然的脚步,拒绝用“模拟”春天来欺骗观众,而是把大自然本身所提示的最美好的一切奉献给了他们。
如果我们尝试去悉心倾听环绕在我们四周的生灵,用我们的心灵去感受生命制造的种种声响——我们会发现它们的数量意想不到地庞大,进而意识到并没有现成的乐器能复现这些音响。不妨想一想城市的嘈杂、工厂的噪音、激动的人群的喧嚷。大自然中所有这些声响都在等待属于它们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和帕格尼尼,#pageNote#3但是只有戏剧会发现它们,而它们也是为戏剧服务的。不管职业音乐家觉得这事听起来多么可笑,未来的戏剧一定会充斥着新的乐器和新的音响组合。剧院甚至会创造一个音域和一种全新的节奏——与节拍器无关,而是人类情感、心灵和
精神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