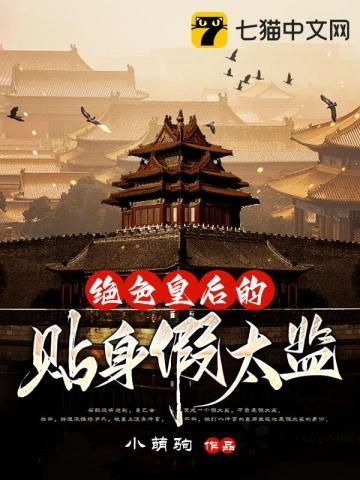凤阅居>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的意思 > 第23节(第1页)
第23节(第1页)
“这不是您用来放首饰的那只盒子吗?”银瓶惊讶的道。
上次玉蕊还东西时,她亲眼看到自家姑娘从那些东西里面挑了三支玉钗放到里面。
不过后面她就再也没见过这只螺钿盒,还以为是很珍贵的东西所以被姜予微给收了起来,没想到竟然是给她的。
姜予微又往前递了递,银瓶这才迟疑的接过。
里面除了那三支玉钗,还有一直嵌紫玉兔金簪,一支白玉如意纹金簪,一条红玛瑙项链和一对碧玉手镯。盒底还压着一张百两银票,以及十锭十两的银子。
她瞬间瞪大双眼,忙盖上盒子还了回去,“姑娘,这太贵重了,奴婢不能要。”
“如何不能?你跟在我身边多年,情同姐妹,这是我为你准备的嫁妆。”
“什么?”银瓶呆愣的看着她,喃喃道:“嫁妆?”
姜予微从袖中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卖身契,道:“这是我前日专程去母亲那要来的,现在还给你。银瓶,你自由了。”
银瓶也认得字,借着昏暗的火光,她清晰的看到“卖身契”三个子,末尾还有她爹的签字画押。
可她却感觉不到半分高兴,泪眼婆娑的看向姜予微,捧着螺钿盒不知所措,也没有去接,只哽咽道:“姑娘,您不要奴婢了?”
姜予微失笑,“你在说什么胡话?我怎么可能不要你?”
暮色苍茫,晚风习习。她转头看向庭院,那种山樱已经挪走,锦蕙也如计划的那般拨去了外院。窗前空荡荡的,还有些不习惯。
“你自小长在溧州,父母亲朋都在这里。我怎能如此自私,让你随我背井离乡?”
“可奴婢若是走了,姑娘您身边连个可靠的人都没有,还是让奴婢跟着您吧。”银瓶心里其实早就有所准备,尽管她也不想离开。可是为了自家姑娘,她愿意追随到天涯海角。
姜予微鼻头发酸,动作轻柔的替她整理了一下额间的碎发,眼睛潮湿,郑重的道:“银瓶,谢谢你,但我不能这么做。”
“为什么?!”
“我知道你与你表兄感情甚笃,你表兄多年未娶也是在等你。”
说起表兄,银瓶的内心也开始挣扎起来。
姜予微又道:“你表兄我见过了,为人襟怀坦荡,谦虚内敛,是个可以托付之人。假以时日必能建功立业,到时你也是官家太太了。有情人难得相守,我和则谦哥哥就。。。。。。银瓶,这也是在成全我自己,你明白了吗?”
“姑娘。。。。。。”银瓶哑着嗓子抽泣,泪水顺着脸颊一滴滴坠落。
“好了好了,快别哭了。”
姜予微本来是不想哭的,可是被她带的也忍不住垂下泪来。她胡乱用手擦掉,故作轻松的笑道:“说起来,我还有一事想要拜托给你。”
“姑娘请说。”
姜予微又拿出一只鎏金梅花纹锦盒,是上次方妈妈送来的。
“外祖父和外祖母年事已高,不过那边有舅舅照料,我也能放心。这只锦盒里的东西我已经挑过一遍,剩下的都是我母亲的遗物,我想请你帮我埋在我母亲的坟前。”
银瓶忽然涌起一股不详的预感,怔怔的道:“姑娘,是不是出什么事来?为何。。。。。。为何奴婢感觉您像是在交待遗言一般?”
姜予微愣住,随即回过神来,扯起嘴角笑道:“什么遗言?你姑娘我此去是享受荣华富贵的,你该为我感到高兴才对。”
她越是这样说,银瓶反而越不安。京城虽然远,可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再回来。
烧掉嫁衣,安顿亡母遗物,还不让她跟着,桩桩件件分明是在诀别啊。
银瓶慌了,拉住她的衣袖声音发颤,“姑娘,您别吓我。”
姜予微叹了口气,拍了拍她的手安慰道:“傻银瓶,放心吧,我决计不会做傻事的。”
“那你发誓。”
“好,我发誓。”
她举头望越,眸色幽沉,须臾渐渐坚定下来。
她姜予微发誓,此生绝不会轻易认输,更不可能成为他人的掌中玩物!
四月二十二日,溧州府的城门前。
天色尚早,日薄桑榆,来往的行人络绎不绝。有的是住在城外的农户,挑着自家种的瓜果蔬菜道早市上来卖,也有留宿在城中的行脚商驾着驴车赶往外地走货。形形色色,熙来攘往。
溧州府的城墙是用黄砖层层夯实而成,足有数十丈高。两扇朱漆柳木的大门,每到寅时五刻便有当班的衙役敲响晨钟,开禁通行。
门前的大街上,有好几辆马车停靠在路边。为首的正是陆寂那辆乌木雕花的安车。
姜家人和贺鄞都来给她送行,乌泱泱的站了一大片,唯独姜氏没来,听说是受到惊吓后病得起不来床了。
她这次可谓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赔了夫人又折兵。谁能想到陆寂会如此不给她颜面?
不过贺鄞倒是一如往常,见谁都笑脸相迎。
杨氏紧紧握住姜予微的手,依依不舍道:“微姐儿,去了京城后一定记得来信,别忘了你永远都是姜家的女儿。”
说完,用帕子拭去好不容易挤出来的两滴泪,装的那叫一个情真意切。
“母亲放心,我永远都不会忘。”姜予微笑了笑,不动声色的把手抽回来,然后看向姜益平。
姜益平眉头拧在一起,到底是自己亲生的女儿。虽然不喜,但终归有些不舍,脸上难得的露出几分离愁。
“身为女子,当恪守三从四德。今后你当好生侍奉陆大人,不可松懈,更不可像在家中这般肆意妄为了,可明白了?”
姜予微原本就不抱希望能从他嘴里听到好话,闻言平静的道:“知道了爹,女儿心中有数。”
哭的最伤心的当属银瓶了,这丫头也不知是不是从昨晚开始便一直哭到现在,双眼肿得如同核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