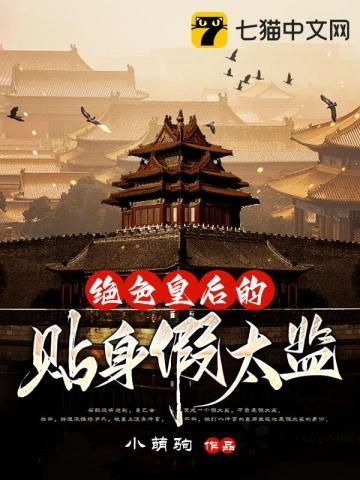凤阅居>绑错抽卡系统后我抽出个动物园 沈闲辞 免费 > 第53頁(第1页)
第53頁(第1页)
還算完好的建築內,一個稍顯瘦弱的人影被另一人掐著脖子,狠狠地摜到了地上,掐著脖子的那人身形壯碩,眸子血紅,雙唇染血,牙齒也被血液染紅,只是不知那鮮血是他自己的,還是別人的。
被他掐著脖子的那個人因為呼吸不暢,眼睛正不停地翻白,兩條腿努力地掙扎著,指甲在那個壯碩男人的手背上劃出了一條條的血痕,喉嚨里也發出了「赫赫」的聲響,眼看著他的掙扎逐漸變得微弱,那個壯碩的男人猛地鬆開了手。
肺部湧入鮮的空氣,那個瘦弱的男人張大嘴巴,用僅剩的力氣拼命攫取著來之不易的空氣,他的脖子上滿是的淤青,但還沒能呼吸幾秒鐘,就又被那個壯碩的男人掐住了脖子。
那個壯碩的男人像是貓逗老鼠一樣,一下一下,緩慢地收攏著掌心裡的力道,一點一點地將窒息的痛處加諸在他的身上。
而那個被掐著脖子的人,大概是在一次又一次瀕臨死亡的窒息中,大腦逐漸缺氧,人也變得混沌不清了。
聶珣走進來的時候,恰好撞上那個壯碩的男人鬆開掐著脖子的手。
「誰!」壯碩男人猛地扭頭,神情不善地看著走進來的聶珣。
聶珣抬眸打量了一下這座還算完好的建築,最裡面,附近沒有窗戶的地方鋪著一張毯子,此時那毯子的大半被血液浸透,那附近還有散落的血肉。
「你是他們的領?」聶珣沒有在意那個壯碩男人的神色,平靜地問道。
壯碩男人警惕地看著聶珣,千百次與人搏殺的經驗讓他本能地將身體擺出了進退皆可的姿態,他的本能告訴自己,眼前的這個男人並不好惹。
在被那個瘦弱的男人趁亂捅刀子的時候,他只是覺得有些好笑,甚至還有閒心慢慢地把對方給玩兒死。
但是面對聶珣的時候,這個壯碩的男人,心底卻不由自主地升起了一絲寒意。
他隱隱約約有一種預感,或許他的生命,就要到此為止了。
多年來,他就是憑藉著這樣野獸一樣的直覺活了下來。
他收下的人殘忍、嗜血、甚至連失去戰里的同伴也會毫不留情地殺掉,又如何會不時時刻刻想著推翻自己呢?
事實上,這個壯碩的領本身就是通過血腥殘忍的手法殺死了上一任領,又以一種殘酷暴虐的統治手段馴服手底下人的。
這樣的威懾足夠強悍,卻註定不會讓底下的人信服,他們只會在覺得自己能力足夠的時候,就去挑釁現在的領,能殺掉,那他們自然會成為的領,而一旦失敗,等著他們的只有被殺死後分食這一條路。
鑑於這樣嚴重的後果,其實有膽量挑釁領的人並不太多,他們更需要防備的其實是同伴。
也是因此,那位壯碩的領對那個瘦削男人的行為分外不解。
因為那個瘦削的男人向來是膽小的,如果不是被領天天帶在身邊,大概在就被他手底下的兄弟拖出去肢解了。
雖然那位壯碩的領總是將那個瘦削男人帶在身邊,但更多的卻是出於惡味,尤其喜歡往他的嘴裡塞人肉,欣賞他驚恐的模樣,有的時候,他總不肯吃,領便會捏著他的脖子將肉給塞進去,直到確認那肉進了他的肚子裡才會滿意地點點頭,欣賞著對方憤恨、絕望、恐懼卻又無可奈何的模樣。
領很喜歡這樣逗弄那個瘦削又可憐的男人,其實他以前沒有這麼瘦弱的,但是在塔蒙聚落生存的那段時間,硬是讓他變得比以前更瘦了。
大概是因為那個瘦削的男人每次都不敢反抗,時間久了,領也膩味了,覺得他壓根不敢對自己出手,便放棄了對他的警惕。但更多的,其實是對自己實力的絕對信任。
卻沒有想到,就在今天,那條領覺得已經被馴養地聽話的狗兒竟然敢朝著自己張嘴了。
更讓領沒有想到的是,在自己教訓那條不聽話的「小狗兒」的時候,竟然還會有人來打擾。
而最糟糕的,是領對能夠打贏那個人,沒有絲毫信心。
明明那個男人看起來不如自己強壯,也不如自己有威懾力,更不如自己瘋狂。
他看上去很平靜,也很閒適,仿佛這座建築不是交手的戰場,而是自家安靜的庭園,而他,只是漠然地看著闖入了庭園的不之客。
不能拖,必須戰決。
那一瞬間,領的腦海里只有這一句話。
領先將腳邊的瘦削男人踹了出去,免得那隻「小狗兒」礙手礙腳,但他的注意力卻一直都沒有從聶珣的身上轉開。
「我叫聶珣。」聶珣緩緩開口。
「聶珣?」領神色凝重地道,「我沒聽說過這個名字,你來自哪個勢力?為何要與塔蒙聚落為敵?」
「很簡單,因為你們占據了我們辛苦打造的聚居點。」聶珣語氣平淡。
領眸子一凜,「殺了巴里和他收下的人就是你?」
聶珣輕輕頷,「如果你說的是之前來過這裡的塔蒙聚落強盜的話,確實是我們殺的。」
「你們既然決定在這裡聚居,那也就意味著你們已經找到了那條乾淨的地下水脈。」領沉聲道,「朋友,如果你願意的話,我們可以和你們共享這條水脈。」
聶珣忽然笑了起來,他饒有興地打量著那個試圖和自己商量的領,淡笑著開口,「我以為,你已經明白了自己的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