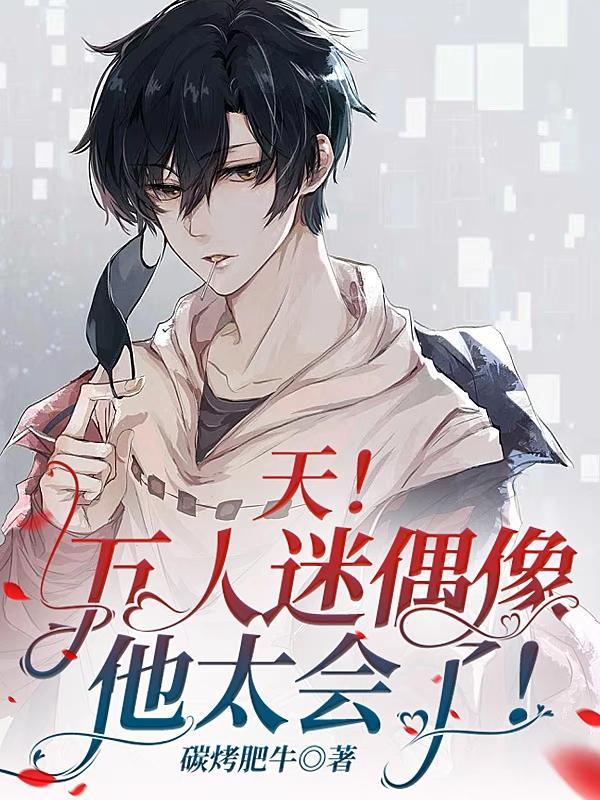凤阅居>缠香花 > 第13頁(第1页)
第13頁(第1页)
沉睡的狼狗不知在何時甦醒,現已將她壓在身下,鐵掌牢牢掐住了她纖細的脖頸。
謝折眼底猩紅,周身汗氣騰騰,上身肌肉緊繃成了警惕待戰的堅硬模樣,鼻息滾燙粗沉,冷眼直勾勾盯著身下女子。
「是你?」
第8章交手
賀蘭香成了被扼住咽喉的鶯雀,怎麼都逃脫不開魔掌,她熱到潮紅的臉色更加緋艷,本能地去掰扯脖頸上鐵鉗似的手指,仿佛在殊死一搏。哪怕這點力量在對手面前不堪一擊。
謝折鬆開了她。
賀蘭香不住地咳嗽,喉嚨里像被塞了只相思鳥,干啞艱澀,奇癢無比,咳到滿面淚痕方才罷休,大口呼吸著氣,胸口隨之上下起伏。
再抬眼,謝折便已下了床榻,上身著有一件白色中衣,修長手指不太耐煩地繫著衣帶,居高臨下,冷冷睥睨著她。
「我……」賀蘭香雙目淚意未褪,眼波流轉,瀲灩生媚,下意識便將提前想好的說辭宣之於口。
無外乎是她一個小小婦人,嬌弱可憐,死了丈夫沒了依靠,擔驚受怕到不行,便想給自己和肚子裡的孩子尋個指望,一時糊塗,便將主意打在了他身上。
賀蘭香的心思何其精巧,她知道謝折留著自己有用,斷不會因為這點小事起殺心,最多把她轟回棲雲閣去,所以極盡扮弱。
「將軍息怒,妾身以後不敢了。」她淚若雨下,兩頰生霞,一副柔弱不能自理的樣子,嗚嗚揩著淚求饒,縱是鐵石心腸也要生出憐惜之心。
「妾身這就離開,不污將軍的眼。」
她撐起酥軟的身段,下床便往門的方向去。
賀蘭香本以為這便能溜之大吉,卻被伸來手臂一把攔住。
眼前人的臂膀是她想像不到的壯碩,在榻上能將她囹圄懷中,下了榻,亦能決定她的去留,和生死。
謝折垂眸,瞧著這身量只與自己胸膛齊平的小小女子,眼中血絲未散,與極黑的瞳仁相襯,陰翳可怖,冰冷無光。
「說的什麼,再說一遍。」他沉聲道。
賀蘭香僵了淚容。
她自詡伶牙俐齒,說話向來有條有理,不至於表述不清,只當謝折沒聽仔細,耐著性子將方才的情形又演了一遍。
話音落下,半晌過去,擋在她身前的胳膊依舊沒有收回。
賀蘭香徹底不明白了,她心想難道這謝折是個聾子嗎?
不至於吧,當時臨安府尹罵他,他聽得倒是怪清楚,還把人家舌頭割了。
昏暗搖曳的光線中,心懷鬼胎的美人抬起臉,輕輕啜泣著,用秋水般的眼眸與那雙陰戾黑瞳對視上。
謝折神情肅冷,不像是耍她。
他是真的沒聽清。
賀蘭香眨了下眼,懸在長睫上的淚珠隨之而落,忽然輕踮腳尖,順勢將唇瓣湊到了謝折的左耳耳畔,聲若遊絲,吐氣幽蘭地道:「我的將軍,我說,我想勾引你啊。」
房中跳躍的燭火似是一暗,淡淡菸絲在潮熱中翻湧。
賀蘭香放平腳跟,依舊是那副楚楚可憐的神情,眼皮稍掀,淚盈盈地瞧著謝折。
謝折表情未變,只有額頭青筋隱約在跳。
他盯著賀蘭香無辜瑩潤的眼睛,胳膊放下,從嘴裡乾脆利落地吐出一個字:「滾。」
賀蘭香含淚轉身,嘴角笑意難以抑制。
出了門,她迎面撞上行色匆匆的崔懿。
在崔懿呆滯的注視下,賀蘭香淚珠漣漣,以袖掩面道:「勞煩崔副將也替我向將軍求求情,我只是想將我夫君的屍骨好好安葬而已,他人都死了,活人又何必與死人計較呢,將軍英明神武,難道連這點小小要求都不能施捨與我嗎?」
崔懿聽的一愣一愣,連她怎麼進來的都忘了問了,只管點頭。
賀蘭香嬌滴滴的一福身,道完謝便往棲雲閣的方向走去。
棲雲閣里,細辛與春燕快要將她找瘋,猶豫要不要將此事通傳時,賀蘭香便慢條斯理的自己回來了。
「有什麼好慌的,」她懶洋洋地臥於榻上,闔上淚痕已乾的雙目,慢悠悠地道,「睡不著覺,出去透透氣罷了,值當大驚小怪。」
細辛緘默,她有種直覺,她覺得主子絕對不是出去「透透氣」那麼簡單,可又不敢多問,醞釀半晌,只好略帶埋怨地道:「這裡外那麼多的守衛,奴婢都不知道您是哪來的本事出去的,他們竟也肯讓您出棲雲閣的門?」
賀蘭香輕輕笑了聲,疲倦襲來,嗓音便越發的軟媚,咬字似斷還連地說:「再嚴苛的守衛,也是生了顆男人心,我一個無依無靠,懷有身孕的柔弱婦人,只是想散散步,又不是去將天捅塌,他們有什麼好攔的。」
細辛知她是在避重就輕,再問也問不出什麼好歹,便嘆了口氣,將被子搭在她小腹上,叮囑她切莫多慮,歇息要緊。
賀蘭香「嗯」了聲,鼻音濃重,顯然困意已至。
在細辛即將退下歇息時,她又跟想起什麼似的,黏糊糊地啟唇道:「對了,明日差人給我裁身素衣回來,我男人死了,我好歹得給他守上三日孝。」
後罩房。
房中藥氣蔓延,與女子身上殘留的纏綿甜香融合在一起,氣息既冷又妖。
崔懿沒想到謝折這麼快便醒,更沒想到竟能在門外撞上賀蘭香,回憶起那女子梨花帶雨的模樣,說完正事,崔懿便道:「看不出來,那賀蘭氏竟還是個痴情女子,自身尚且難保,便惦記著將謝暉妥帖安葬。大郎,我知你對這家人的恨已入骨髓,不過既然人都死了,便賞具棺材,全了賀蘭氏的念想,權當可憐她了。」
小貼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或推薦給朋友哦~拜託啦(。&1t;)
&1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