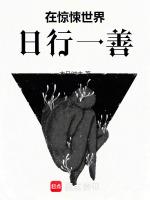凤阅居>红尘仙侠 > 第91章 往事如烟(第2页)
第91章 往事如烟(第2页)
“不对,有另外计划没错,却不见得是要把其他人都杀了。”
“哦?”许兴全被他一点,似乎也抓住了一些想法。
“是因为薛蟾。”
“此话怎讲?”
“金蟾印信、严锦绣、薛家,所有线索串联在一起只有一个指向,那就是薛蟾。凶手的动机肯定就是薛蟾,其它不过只是掩藏真相的浓雾罢了。”
“你想的没错,然而我们也调查过薛蟾。薛蟾的底子很干净,为人正直又从不拈花惹草,但凡与他有关的人,无一不是念着他的好。哪怕是到了今天,那些人也都在觉得这是老天爷妒忌,才这么早早收了他。”
林云摇了摇头,“我没说凶手的动机是仇恨。凶手对严锦绣有恨,对薛蟾的动机却不一定。”
“哦?”
林云没再继续。
“对了,许大哥说‘薛家救济过的人数不胜数’,是怎么一回事?”
李蓦连忙插进话题,道:“唉呀,小兄弟不是本地人,难怪不知道。原本青城最大的善堂,就是薛家开设,结果薛家一倒,善堂资金周转不灵,也没人愿意接管,所以便这么荒废了。如今那里尽住着些乞丐了。”
“善堂?”林云摸了摸下巴,反问李蓦:“善堂查过吗?”
“查过,但是善堂里全是受薛家救济的人,跟薛家没有仇。”李蓦答道。
“升米恩斗米仇,事实很有可能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
“小兄弟说得在理。”许兴全道:“只是当年查过所有跟薛蟾有关的人,善堂里的人,都没有作案的时间。”
“婚宴时在场的呢?”
“没有去而复返,都是结伴而归,路上可以相互作证,到了家也有门房跟下人作证。”
“总共几人?”
“三人。”许兴全脱口而出,而后猛然又记起了什么,匆忙补充道:“薛蟾交友很少,六月初一送帖时原本是四人,但有一人后来恰好得了时疫,被看管了起来。对了,好像就死在薛蟾大婚当天一早。”
红眼、时疫、大婚当天病殁,实在是太巧合了。
许兴全说到这,脚步猛然间顿了顿,显然也是意识到当年的疏漏竟是在这里。
毕竟谁会想到去查一个“死人”有没有杀人的动机?
“小兄弟的意思,这个人……”许兴全兴奋得满脸通红:“李蓦,去查查当年疫病馆的记录。我记得当年得了时疫无法救治的人,都埋在了南郊。去查!”
“是,师傅!”
许兴全急着往外走,林云却拉住了他的袖子。
“来都来了,不急在一时。周觅当时藏身的那口枯井在哪里?我觉得他俩极大可能并不无辜。还有当年的案子最后是怎么结案的?”
“当年的时疫并非无药可治,只不过药材昂贵,所以死的都是些穷苦之人。后来官府觉得,应该是得了疫病之人借着婚宴热闹混进了薛府,因为无钱医治所以动了歹念,杀了人,抢了薛府的库房。”
林云没有再问,许兴全的话里话外,当年薛府灭门,应该是丢了些现银,所以官府索性把案子定性求财杀人。
如果不是自己掌握着金蟾印信,又知道了这么多内情,说不定也会这么以为。
印信这种物件,很难脱手。
当年盗走薛府钱财之人连饰都没动,只拿了银子,怎么可能盗走印信?哪怕它是纯金。
“不合理。薛府宴客少,哪有什么人多,犯人根本混不进去。”
看来这案子结得相当草率。
“当时衙门也觉得不合理,不过一桩案子拖了两三年,又恰逢京察,再没有结论实在是没办法交待。”
许兴全面露窘迫,因为涉及的事情太过敏感,索性岔开了话题:“枯井在偏院,当时确实是我带人找到奄奄一息的周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