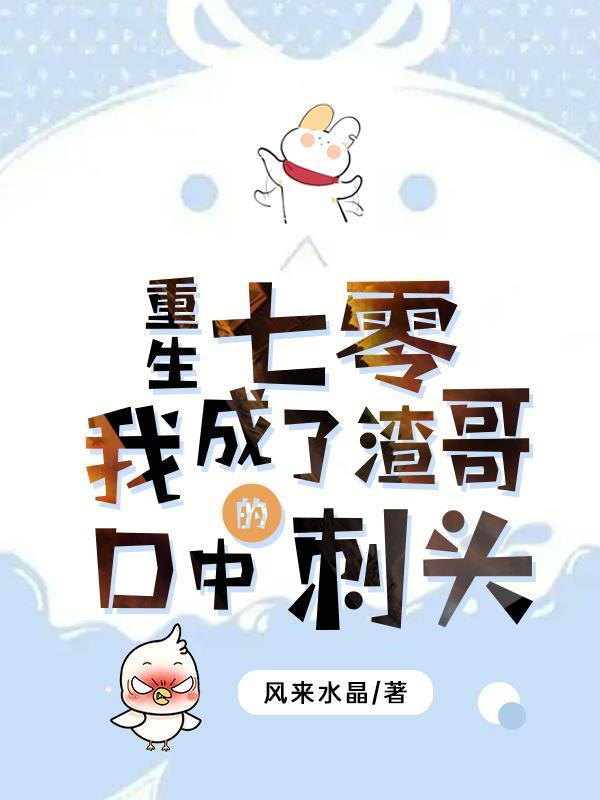凤阅居>哨向设定是什么 > 第8页(第1页)
第8页(第1页)
还没走到最里面就听到破空声和利器没入肉体的沉闷声响,还有隐约可闻的闷声哀嚎。席枫眉梢一挑,觉得有些鲜。
时恪的身份他是知道的,a级哨兵,s级雇佣兵,以他的手段,开店之前应该打点好了,不会有不长眼的敢到这里来闹。
走到最底拐弯,几根生锈栏杆后的场景一览无余。
时恪坐在沙上翘着腿,指尖夹着一根电子烟,席枫鼻尖嗅嗅,闻出来里面的烟弹是价比黄金的哨兵安慰剂——不能代替向导素,但能产生拟精神抚慰作用,有一定成瘾性,算是灰色地带的商品。
地上的男人瑟瑟抖地蜷缩着,身上没有束缚却好像动弹不得,除了插着四支飞镖和一身灰尘,甚至连一点血迹都看不到。席枫上前仔细看了两眼,瞳孔散大,呼吸急促,肌肉紧绷,典型的极度惊惧症状。
“东西哪来的。”
温厚低沉的声线染上冷冽的杀意,时恪没有看席枫,垂眸把玩着手里的飞镖,一只狞猫窝在沙上慵懒地舔着爪子。席枫毫不怀疑,下一支飞镖出去就要带走这条命。
“我我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啊啊啊啊!!!!”
地上的人哆嗦了两句突然尖声大叫,然后又像是被什么扼住了脖子一般戛然而止,竟然昏过去了。
淡淡的骚臭味升起,席枫嫌弃地把视线从地上的污秽物上移开,抬腿踢踢身边人的小腿。
“说说吧,怎么回事儿啊,动这么大肝火。”
时恪按下沙扶手上的一个按钮,立刻有两个黑衣人进来无声而迅地把现场收拾干净。
……
席枫一直觉得时恪应该少看点日漫,真的。
“瞅瞅。”
时恪没理他的内心吐槽,丢过去一个圆柱形小瓶,里面湛蓝的液体晃动着折射灯光,颜色漂亮地像是为小姑娘们特调的苏打水。
“什么东西,毒品?”
席枫打开木质瓶塞,手掌扇动问了下气味,是一种清爽的果木香,闻起来没有丝毫危险。
“别闻太多,这是最型,我以前见过。”
时恪说的见过,不是在路上或者哪个酒吧里随便看一眼的见过,而是在执行某一场雇佣任务的时候,曾经见过,更有可能不只是“见过”。
“这玩意有什么特别的?”
“不算很清楚,不过应该跟哨兵有关,沾上了很麻烦,也不知道怎么混进来的。”
席枫对时恪的手段清楚得很,刚才那人,就算脱光了也看不出伤口,但要是拉去拍个片子,就能看出来离领便当也不远了。
“走吧,开门了,你都问不出来,估计是个毛头混混。”
“希望吧。”
时恪起身,狞猫伸个懒腰踏着步子跟上去,在即将触碰到他脚跟时消失在空气里。
事实证明席枫想得过于天真了,他在吧台喝着时恪调的酒,舞池里突然起了骚乱,尖叫和叫骂一时压过震耳的音响。
人群散开,显出两个高大男人扭打的身影,时恪慢悠悠擦着杯子,仿佛无事生。
席枫喝完最后一口,起身解下袖扣放在桌面,心里把时恪拿自己当打手的行为唾弃了十遍,还是不情不愿地上前。
没办法,时恪下手太狠,大庭广众弄出人命不好交代。
随手抄张凳子把其中一人打倒在地,侧身避开后方的直拳,矮身一记肘击正中身后人胸骨角附近的胃部。前后不过几分钟,方才还气势汹汹的两人就一个抱头一个抱肚子倒地哀嚎。席枫上前尽职尽责地查看了两人的情况,诧异地觉这两人的身体表面有一定量的精神力包裹,以头部为甚。
这种情况席枫还是第一次见,他只是治疗普通人的医生,在这方面并没有知识储备,索性随意挥手叫来两个服务生把人带下去关着,其他人动作迅地收拾残局。
场面一时突兀得安静,席枫拍拍衬衫折痕,不知从哪顺来一支麦克风单手翻上舞台,“一点小插曲,大家该吃吃该喝喝,今天全场六折,我先干了!”说罢从身边侍者托盘上拿过一杯深水炸弹一饮而尽,些许酒液顺着纤长脖颈淌入领口打湿衬衫,音乐在最后一口适时响起,席枫将杯口朝外展示半圈,丢个飞吻就把舞台让给舞女了。
“不用谢我。”
“一晚上亏了好几万,搁那跟谁客气呢?”
……席枫毫不顾忌形象地比个中指,半趴在吧台有点懵。虽说他常泡吧,其实酒量相当一般,慢慢喝还好,像刚才这么灌水似的,喝不了两杯就头重脚轻找不着北,今晚为了救场也是下了本钱。
“刚才那两个怎么处理,报警?”
时恪没说话,半晌揉揉眉心,“你先回去吧,我来处理。”
席枫一脸不放心地反问:“你……哪种处理?”
“……合法那种。”
时恪忍着没给他一拳,随手叫人开席枫的车把他送回家了。
作者有话说:
单机更(66)
如果有人看的话,可以给点评论吗……
手头存稿不多了,如果没人看会适当放缓更度
第七章
起床时带着点醉酒的头疼,席枫喝下一碗醒酒药,赶到医院食堂吃了早饭。
开晨会的时候院长把他好一顿夸,催他赶紧交篇论文出来,争取今年就升主任医师,大有一副定他为继承人的样子。席枫嘴上应着,心里却暗暗苦,他宁可做十场手术都不想写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