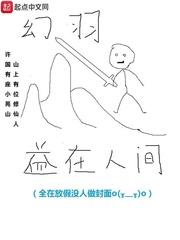凤阅居>主角他怎么还是变偏执了by > 第204页(第1页)
第204页(第1页)
只听她说道:“如果你当时看了她一眼,是不是就不会把她摔死了……”
如果那个时候,你没有那样做,那该多好啊。
“我一直在等你,每天都在等你,从白天等到晚上,一天又一天,等到我的容儿都快出生了,你都不回来。你去哪里了啊?你去做什么去了啊?”
“我等了你好久,一直等到我的容儿出生了你才回来。可你为什么要那么做?我只是累得闭上了眼睛,又不是晕了过去,你为什么要把我的女儿摔死?就为了不让人怀疑那个野种的身份吗?”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以为我没看见吗?”
“……”
她的声音一直很低,越来越低,眼里像是噙满了鲜红的血,可表情却透着股冷漠,连说话声都冷冷淡淡的。
她冷冷淡淡地说着那些话,重复着那段无论怎样都过不去的过去。
他摔死她的容儿,所以她也想弄死他的景容。
可是景容太小了,那么小一个,路都不会走,就整日跟在她身后,追着她,撵着她,用稚嫩生涩的声音一遍遍喊她“母亲。”
她真的很厌恶那个小孩子叫她“母亲。”
她想她是厌恶的。所以她的所作所为,从来都是那样的直白,她从不掩饰对他的厌恶和冷漠。
没有人是无辜的。
景容从来都不无辜。
在晃了片刻的神后,萧棠收回心神,目光重新聚焦在眼前的男人脸上,嘴角渐渐勾起笑意,然后缓缓站了起来。
景容不无辜,是的,但是,有人更该死。
以前她做不到,无从反抗,可现在不一样了,他已经虚弱得快死了。
随着她缓缓站起的身体,手中的东西也从血池中显露出来。
是一把剑。
一把看起来普通而又精致的剑。上面缀满了宝石,却一直沉在这种阴暗恶臭的地方,它见不得光的样子,像极了有些人的人生。
萧棠微微笑着,眉眼弯弯地道:“你送我的,还记得吗?”
空气里伴着似有似无的血腥味,这一夜尤其漫长,好像总也不见天亮。时辰未至天明,夜空还一片黑暗,但在遥远的天边,却亮起了一大片比朝霞还亮的云彩,像天降异象一样。
这样的动静引得山下的人们纷纷开门出来看,他们披着外袍,在深夜里呼朋引伴:“快来看,那边是景家的方向吗?”
年纪小些的孩子好奇地望着天边,吵吵闹闹地问道:“好亮啊,是……是朝霞吗?”
身旁的大人缓了缓眉眼,皱眉道:“不,是起火了。”
--------------------
这是场从地下室蔓延上来的大火,在火势最盛,几乎照亮了半边天的那一刻,十道光芒划过夜空,如流星一样落往大火源头。
因火而起的亮光渐渐熄灭,天边的亮光却从地平线缓缓升起。
萧棠的居所付之一炬,连带着大殿,也都崩塌了,只剩下一片残破的黑色废墟。为了灭掉这场火,长老们损耗了不少灵力,因此准备暂且先回去休息,将剩下的都交给弟子们处理。
什么都烧毁了,什么秘密也都该被埋藏起来了,可总有大火毁不掉的痕迹。在地下室的入口被发现后,温故就立马意识到了些什么,然后赶紧让林朝生把长老们叫回来,并让其他弟子原地待命。
在告知了长老们地下室里面可能会有什么之后,大长老沉默片刻,当即决定独自进去查探,因为下面若真有禁术,现在也只有他才有能力将其封印。
大长老进入地道之后,天色渐渐变得亮了起来,但看这天色,实在不像个晴天,反倒阴沉沉的,像是随时都会下雨。
温故抬起头,望向绵软阴沉的天空,突然间意识到天气已经完全变暖了,好像又要到曾经那个经常下雨的季节了。
一如他在后山捡回景容的时候。
好像过去了很久,又好像就在昨天。
大长老这一趟去了很久,久到不知道是一个时辰还是两个时辰都过去了,还不见出来。其他长老等得急了,就想下去看看,看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毕竟牵扯到禁术,得重视起来,有的禁术过于邪门,是会困人的,把人困在里面,出也出不去,只能等着被禁术一点点吸纳。
这样邪门的禁术,以前不是没有出现过。
正当他们走到地道入口,俯身准备进去的时候,就见大长老一脸沉重地出来了。他走得慢,出来后又驻足回首,沉着眼睛看了那道入口好一会,深深叹了口气,然后说道:“以后有的忙了。”
的确有的忙了。
先前景家那些常常无故失踪的弟子,十有八九是命丧于此,以景家在修仙界的地位,总要给那些家属一个交待。至于怎么交待,长老们各执一词,说着说着就有了多种解决方式,或是隐瞒真相然后暗中照顾其家人,又或是告知真相并赔偿……
但大长老并没有参与讨论,而是缓慢地走到景容面前,用着有些低哑的声音说道:“禀少主,下面除了一些弟子的尸骨外,我还看见两副被烧得看不清模样了的尸首,一男一女,身形很似家主与其夫人。”
说到这里,长老微微停顿了片刻,然后才继续道:“男子受了剑伤,虽不致命,却流血过多,从一个暗房一路爬出来,最后被烧死在了靠近地道出口的地方。至于那名女子,则是被人用剑从她身后刺进了心脏,一剑致命。”
从回到景家之后,景容就远远地站在一旁,没有说一个字,连动也没有动过,一直安安静静地望着眼前这片废墟。